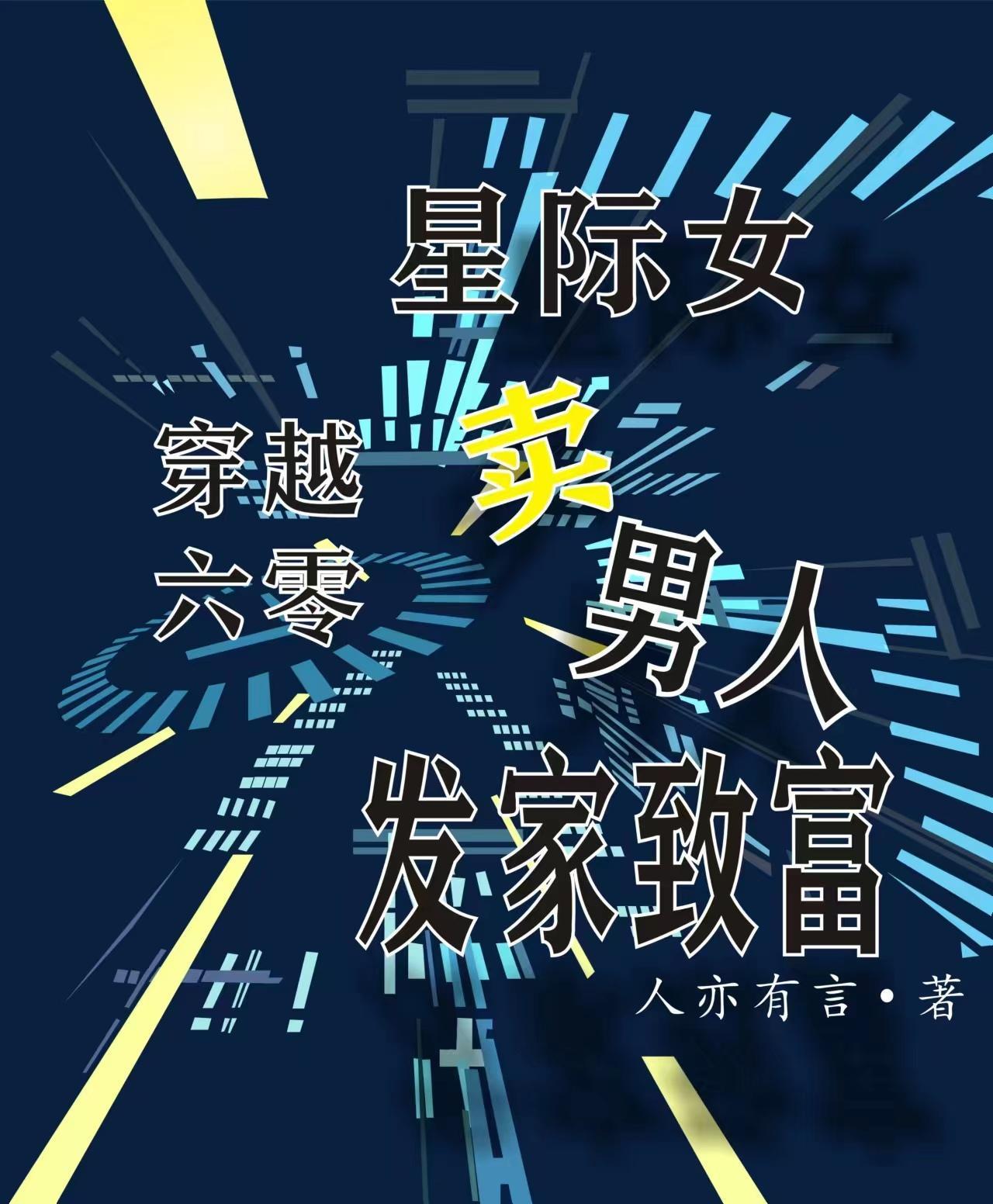笔下中文>好好地活 > 第503章 九妹来访(第1页)
第503章 九妹来访(第1页)
赵小禹召回了铲车司机,又从房宇集团的工地上请来一名技术员,让他拿着水准仪测绘和找平土地。
技术员问:“赵总,你这是要建什么?”
赵小禹说:“种地。”
技术员说:“赵总你太牛了吧,种地都这么精益求精的。”
赵小禹说:“用工业的手段种地,这就叫做农业现代化,我将来还要用飞机飞播,搞人工降雨。”
“真的假的?”技术员有点不信。
赵小禹也笑了。
不过,精益求精,倒确实是他的要求。
土质不好,水资源紧缺,他要尽可能地把地搞得平整和水平,以使每棵庄稼都能雨露均沾,得到雨水和粪水的滋润。
辛苦了半个来月,种的地和盖猪舍、盖房子的地基都搞好了,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搞钱,买一台吸污车,请工程队,购置生产原材料。
赵小禹正蹲在山头盘算的时候,山路上出现了一辆红色的汽车,随着起伏的山路忽隐忽现,宛若一团跳动的火焰。
片刻后,一辆红色的路虎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他笑了,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,正在打盹,就有人送来枕头了。
他早已计划好了,用商品混凝土建猪舍和房子,省时省力又耐用,随便去哪家搅拌站赊几车混凝土,三两天就完工了。
这几年,定东市前前后后建起了几十家商混站,甚至还专门搞了个商混园区,混凝土的价格一降再降,早已不是陈子荣当年开商混站时那种供不应求的局面了,赊账买卖到处有。
盖猪舍用c15或c2o混凝土就足够,中间穿插几根细钢筋,实在花不了多少钱,大费用是在施工上。
赵小禹正在纠结,是请大哥帮忙,还是和外人合作。
请大哥帮忙不是为了占便宜,是免得大哥以后埋怨他见外。
但请大哥帮忙,也挺麻烦的,这么点小工程,对于财大气粗的大哥来说,就是九牛一毛,不,连一毛都算不上,就是放了个屁,吐了口痰。
大哥一出手,估计又是大手笔,不经他同意,就把正规的工程队派来了,把高标号的混凝送来了,本来一块钱的营生,非得干成五块钱的。
给他钱吧,自己没有,也没那个必要;不给他钱吧,又不想欠他这么大的人情。
这回好了,九妹来了,自家人好用。
这段时间,赵小禹竟把九妹给忘了,九妹现在也是大人物啊!
住在许清涯家里那段时间,陈慧给他打过几次电话,要约他吃饭,他拒绝了,并下了命令:“这段时间,不要打扰我,我要专心搞实验!”
陈慧满面笑容地从车上下来,进入三十岁的她,体态越丰腴了,梳着大波浪卷,穿着一件大红的连衣裙。
“九哥,你不回家了?”她边走边问。
“这就是我的家,”赵小禹站起来,指了一圈这片地,“我的家无边无际,海阔天空,海阔凭我跃,天高任我飞。”
“可是太荒凉了,你不孤独吗?”陈慧走到赵小禹面前站定,放眼望着远远近近的丘陵,她的红裙子和长在风中飘舞。
赵小禹说:“心中若有桃花园,何处不是水云间,我没觉得孤独,反而还挺喜欢这里的。前段时间刮大风,那种感觉爽,外面刮的风越大,我在屋里睡得越香。”
犹豫了一下,又说:“九妹啊,你在酒池肉林中,被人前呼后拥,自然体会不到这种空旷的意境。”
转而又说:“再说明年我把养猪场搬过来,人欢猪叫,怎么会孤独?只怕太吵了。”
“唉,你宁愿和猪在一起,也不肯和我在一起。”陈慧酸酸地嘟囔道。
“这话说的,什么叫我和猪在一起?”赵小禹嗔怪道,“我搬的可不只是一个养猪场,整个家都要搬过来,我妈、老胡、金海、芳芳、小蛇,都要来这儿,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,我们就告别了。”
接下来,赵小禹向陈慧详细讲了自己的设想,带着她参观了这片地,最后回到赵小禹住的那间破烂的工棚里。
工棚确实够破烂的,是用单层红砖盖的,墙面没刮白,只用水泥砂浆抹了一遍,显然有些年头了,到处开着一指宽的裂缝。
屋顶挂着一盏白炽灯泡,上面积满了污垢。
地下铺着红砖,但积了厚厚一层泥土,坑坑洼洼的。
陈设更是简陋,墙角摆着一张木质的单人床,床头破损严重,斑斑驳驳;下面的床箱还开着一个洞。
还有一张写字桌,同样是破破烂烂,一条腿断了,用红砖支着,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的电视机。
当地安着一个炭炉子,当肚上开着裂,火筒已薄如纸,到处是砂眼。
陈慧的眼泪都要下来了,心疼地说:“九哥,你就住在这儿?”
“是啊,”赵小禹没注意到她的表情,“我的安乐小窝。”
走过去坐在床沿上,拍拍崭新的床单,不无炫耀地说:“芳芳买的,都是高档货,有个妹妹可真好啊!来,九妹,过来坐!”
陈慧无心坐,把屋子打量了一遍又一遍,终于忍不住说:“这环境也太差了吧?”
“我没觉得啊!”赵小禹爽朗地一笑,“比不上你给你爸妈盖的新居,但比他们的旧居,还是绰绰有余的,起码不用十来个男女挤在一盘破炕上。”
“那倒是。”陈慧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,干笑了一下,收起了嫌弃的表情,走过去坐到床沿上,拉起赵小禹的一只手,“九哥,那我能不能也来这儿,你要我不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