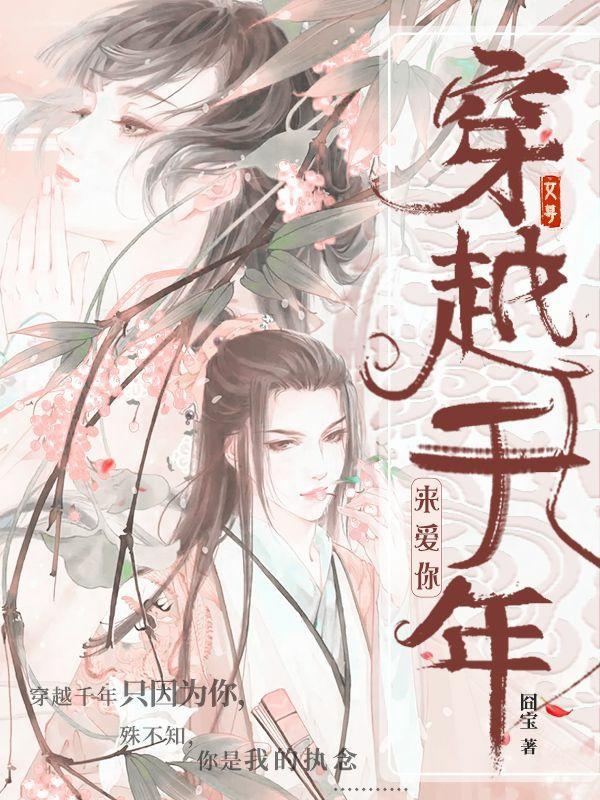笔下中文>山河之下 > 第109章(第1页)
第109章(第1页)
名垂千古又如何?那一刀一剑剜在身上,怎么会不疼?足够礼貌又如何?是战争就一定会死人,要么是你的兵,要么是我的兵。最后的胜利者又如何?那是无数人流血牺牲换来的,也牺牲了无数人的家庭幸福。
所以他讨厌战争。
讨厌,却也不会多嘴。有时候他也厌弃这样的自己,像那种满口仁义道德,遇事却徘徊不前的迂腐书生。
“我们走吧,得赶在天亮前回去。”齐同晏转身,循着记忆往来时方向走去。
“殿下没有其他想问的了吗?”沈宋瓴眨眼,问。
齐同晏看他一眼,说:“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聊天不够舒适,所以还是等到下次再问吧。”
“那下一次聊天时,沈某会给殿下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的。”
二人走着,很快就各自止住了话头,安静地沿着来时路,再一次七拐八弯地绕了回去。
齐同晏重新躺到那个房间的床上时,天窗已经被关好,房间里的陈设与他离去前没有丝毫变化。离天亮不过两个时辰,齐同晏趁着这点时间给自己补了个觉。
天大亮时,门外照例有下人送来早食,齐同晏拉住那人,问:“塔……你们王上呢?”
那人脸色一急,却只是不说话,伸手拽了拽自己的袖子,没拽出去。
齐同晏又说:“你们王上是把你们嘴给堵上了吗?一个两个都不跟我说话,搞得我像什么洪水猛兽蟒蛇毒蝎。”
“小的只是照吩咐办事,公子问再多也没用的,还请公子放过小的吧。”那人的面上带着为难,齐同晏挥挥手便让他下去了。
“不说就不说,我也不缺你那点消息。”齐同晏坐在桌上,恨恨地咬着嘴里的早点,暗自嘀咕。
虽说经过昨天一天的死缠烂打,齐同晏心里已经有了个大概,但他还是不死心。一直到下午,齐同晏在心里确定了,这些人估计的确是被塔呼托下了命令,不许跟他讲多余的话,因此他从他们嘴里是什么都问不到的。
白天逃出去肯定是不行的,太显眼了,门外的人精神也足,警惕得很。晚上就算能潜出房间,城门已经关上,他也没法跟着人混出去。
难道真的只能等到八月十五?等塔呼托把他送回去?
齐同晏坐在铜镜前,思绪乱飞。
突然有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,很快又消失不见。他使劲地回想自己刚刚的思路,总算抓住了那一句话:
——为什么我要顾忌那么多?
对啊,为什么他要顾忌那么多?
客观来看,塔呼托不想要他的命,就算是有目的地把他送回去,那也威胁不到他的生命安全。而且齐同晏总觉得,比起让他死,塔呼托似乎更想他活着。
既然如此,那他有什么好怕的?大不了也只是再被抓回来,大不了也只是真的等到中秋后再被送回去。
打定主意后,齐同晏也不急了,在房里悠着心思欣赏这与昭国不同的装潢风格,一直发着呆到了晚上。
是夜,三更时,一如昨晚。天窗被悄无声息地打开,上方处再一次飘落一张纸条,只是这张纸条上的内容没什么营养:沈某来陪陪殿下。字句的后方还画了一张明朗的笑脸。
这回齐同晏没把纸条烧掉,而是找来笔墨,在纸条的后方写了几句话,随后努力地用动作示意沈宋瓴,把昨晚的绳子从天窗处放下来。沈宋瓴费了好几秒才明白齐同晏的意思,把身边的绳子放了下来。
这个天窗就是这点不好,两个人交流起来费劲得很,你也不能指望对方读得懂暧昧不清的唇语、或是看得清你写在纸上的字。
齐同晏将纸条绑好系在绳子上,扯了扯绳子,示意沈宋瓴再把绳子拉上去。
几秒过后,绳子的末端又被悄无声息地放下来,齐同晏把绳子绕到自己身上绑好,又扯了扯绳子。感受到齐同晏的示意,沈宋瓴开始用力,缓缓将他拉了上来。
有了先前齐同晏写在纸条上的吩咐,沈宋瓴很快就轻车熟路地带领齐同晏潜出别舍,依旧是昨天的路线,依旧是昨天的码头。
码头如今空无一人,更没有任何船只,沈宋瓴吐出一口气,问:“殿下,现在我们去哪?”
“别上大路,找个离城门近的、从缘故上说得通的地方,待上几个时辰。天一亮我们便想办法混入出城的人中。”齐同晏说。
沈宋瓴思考了一瞬,说:“沈某依稀记得,靠近城门处,似乎是有一片十分宽广和茂盛的枫叶林,林中还有座年久失修的庙宇。”其实说年久失修都是抬举,那座庙宇早就失去了人的朝拜与供养,已经是破破烂烂的模样了。
“可以,那我们就小心绕到那片枫叶林吧。”大街上除了巡夜的士兵,还有报更的守夜人,齐同晏不想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。
又是一阵弯弯绕绕的,沈宋瓴带着齐同晏找到了那座破败的庙宇,他正想进去,齐同晏却绕过了那间庙宇,往其他方向走去。沈宋瓴悄声追上,压低了嗓子在齐同晏身边疑惑问道:“殿下?”
齐同晏没说话,一直到走出好些距离,确认再看不见那间庙宇了,他才开口说道:“最好别进去那座庙宇。”
沈宋瓴突然来了兴致:“怎么,殿下是听过什么山野故事吗?跟沈某讲讲如何?”
“那要让你失望了。”齐同晏走近一棵树干,摸索着看了两眼,“我只是觉得,荒芜破败的庙宇基本都是穷途末路者的地方,俗话来讲就是乞丐的歇息地。我们贸然进去,不说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,光是我们这种一看就不属于穷人行列的装束,也足够他们仇视我们了。而当人处于仇视状态下时,他们做出什么行径都不奇怪。”